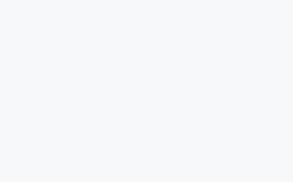 当今一个非常重要且令人不安的事实是,在思考思想和大脑时,人工与自然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自欧洲科学革命期间现代思想诞生以来,心灵及其能力一直被视为与身体、机器和思想辅助技术(例如写作)纠缠在一起,因此人类智能被理解为一种自动性。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David W. Bates做了《21世纪的控制论II:未来的控制论》系列讲座,题为“自然智能的人工历史”,通过对人工智能的分析。批判性分析指出,智力产生于思想与自动性的对抗,而不是来自自动过程本身。
当今一个非常重要且令人不安的事实是,在思考思想和大脑时,人工与自然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自欧洲科学革命期间现代思想诞生以来,心灵及其能力一直被视为与身体、机器和思想辅助技术(例如写作)纠缠在一起,因此人类智能被理解为一种自动性。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David W. Bates做了《21世纪的控制论II:未来的控制论》系列讲座,题为“自然智能的人工历史”,通过对人工智能的分析。批判性分析指出,智力产生于思想与自动性的对抗,而不是来自自动过程本身。
培根曾将自然历史分为“自由自然,按照其正常进程运行;受阻碍的自然,受到一些顽固的、不常见的事物的阻碍,例如畸形生物的产生”和“受人类手段阻碍的自然”。自然受到束缚和影响而产生人造事物”。后者对于培根来说尤为重要,“光靠双手或仅靠智力是无法完成很多事情的。完成一项任务需要工具和帮助,而智力就像手一样需要工具和帮助。正如工具一样,手要么提供运动,要么引导运动,心灵的工具要么为智力提供方向,要么发出警告”。
今天一个非常重要且令人不安的事实是,在思考心灵和大脑时,人工与自然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我们这里理解的大脑本质上相当于一个以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为主导范式的人工神经网络系统。事实上,这是用人工智能的人工神经网络来解释大脑作为一个真正的自然器官的运作。因此,我们不仅将大脑理解为一个计算系统,反过来也将计算机理解为一个类脑系统。即通过神经形态芯片设计,我们将大脑的神经网络系统应用到计算架构中。
大脑是一个自动机吗?
将计算机视为大脑的长期观点使得认知科学从本质上承认,科学地理解心灵的唯一方法是将其视为一台机器、一台自动机。图灵在20 世纪50 年代的人工智能研究中提出了一个观点:“这项研究的前提是,学习的每个方面,或者智能的任何其他特征,原则上都可以被准确地描述。如此之多,以至于机器可以是为了模拟它而构建的。”香农和麦卡锡在《自动机研究》 的“序言”中写道: 我们这个时代最具挑战性的科学问题之一是大脑如何工作。作者感兴趣的是这样一个事实:每个时代都根据当时使用的机器的特征来理解大脑。我们可以追溯到笛卡尔,他相信神经系统可以通过与十七世纪的水力机械类比来理解:“我们可以将我所描述的机器的神经与这些喷泉工程中的管道进行比较。 ……它的动物精神相当于提供动力的水,心脏是水源,脑腔是储水罐。”这引发了一系列关于身体作为机器和大脑作为特定类型的机器(信息机器)的思考——。事实上,在这个时期,一些机器开始带有人工智能的含义,比如布莱斯·帕斯卡发明的滚子加法器和莱布尼茨的乘法器。这说明,在近代早期,尽管人们对机械化、物化思维有所抵制,但自动化仍然形成了潜在的趋势。
19世纪,我们看到了逻辑的形式化和机械化。从威廉·杰文斯(William Jevons) 在19 世纪末发明逻辑钢琴,到查尔斯·皮尔斯(Charles Peirce) 发现可以使用电子开关电路来执行逻辑运算,这导致了逻辑钢琴的新设计,它通过电路而不是机械来运行齿轮。这种将思维和脑机视为一种自动机,以及构建具有我们所谓的认知性能的自动机的双管齐下的努力,引发了19 世纪的辩论——“我们是自动机吗?”观点具有历史意义;它们使机器和思想之间的类比更加接近。
在19世纪,我们有另一种观点,认为大脑与其说是一台思维机器,不如说是一个利用机器进行思考的特殊器官。卡普在他颇具影响力的著作《技术哲学基础》 中指出:“在外部大脑、手和工具中构建了文明。”因此,人类被理解为使用工具来建造东西的文化动物。新的表达形式和新的行为方式。亨利·柏格森和生物学家阿尔弗雷德·洛特卡都持有类似的观点。遵循这一时期的哲学,严格来说,思维并不发生在大脑或头部内部,因此不能像机器一样自动化。
正如维特根斯坦在20 世纪30 年代的笔记中所反映的那样:“有趣的是,对于哲学家来说,最危险的想法之一就是我们用头脑或头脑思考。”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思考是否可以说是心灵的某种特定的有机过程,就好像它在大脑中被咀嚼和消化一样?” 2000年初,一个名为“人工消化”的艺术项目带来了这种概念化。但维特根斯坦感兴趣的是,思考似乎与消化不同。 “我们能否通过用无机过程代替思维来达到同样的目的,就像用假体思维装置一样?我们应该如何想象一个假体思维器官?”这是维特根斯坦提出的问题。
关键是思维如何通过技术外化
人工智能的传统观点是,计算机可以被理解为一个本质上像人类一样思考的巨大大脑。如果我们想超越计算机的特定隐喻,那么,大脑的机器是什么?德国哲学家霍克海默写道:“启蒙技术设备的进步伴随着一个非人化的过程。思想越自动化、工具化,人们就越难看到其中具有本体意义的思想。它们被视为事物,机器……”但从阿兰·图灵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得出略有不同的结论,“‘机器’完全是通过其在连续时刻的可能配置之间的关系来描述的,它是一台机器。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但图灵想思考的是,我们如何才能让计算机这样的机器接受所谓的文化教育,在他看来,文化学习带来的智能并不是印在大脑上的东西,而是大脑的遗忘能力。并做一些不寻常或新颖的事情,这引出了图灵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如果人们期望机器不犯错误,那么它就不可能是智能的。机器必须与人相连,这样才能适应人类的标准。”因此,机器和人一样,不断受到外界的干扰,但它们也在不断地利用自己可塑大脑中的资源来进行自己的行为。对于图灵来说,使认知成为可能的是外部干扰,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称之为大脑的自动化,但同时,大脑总是能够不自动化,能够引入某种不可预测性。性,本身就是智能行为的核心(社科报综合媒体“思想工场”出品,全文请见社科报及其官网)
版权声明:本文转载于网络,版权归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本站编辑删除。